北京疫情,一场没有起点的战争,与无法终结的集体记忆
2022年冬,北京街头核酸检测点的长龙在寒风中蜿蜒,一位老人喃喃自语:“这疫情,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头的?”这个问题,像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人群中激起无声的涟漪,官方时间线指向2020年1月20日,北京市大兴区确诊两例新冠肺炎病例,宣告疫情正式登陆首都,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却发现疫情的“起点”不过是一个被建构的时间标记,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时空叙事与集体创伤。
追溯北京疫情的所谓“起点”,实质是陷入了一场现代性的认知陷阱,人类思维渴求线性叙事,执着于为混沌现实寻找清晰开端,病毒传播的本质是网络状、弥散式的,它嘲笑人类对确定性的执着,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早在官方确认首例病例前,病毒可能已在城市隐秘流动,那些被标记为“起点”的事件,不过是监测系统终于捕捉到信号的时刻,而非病毒真正开始传播的瞬间,将疫情起点定于某一日的仪式性操作,反映了现代社会通过时间标记来驯化不可控风险的深层心理机制——我们将无序纳入日历的框架,仿佛由此获得了掌控感。
北京作为超大型流动枢纽,其疫情“起点”本质上是全球互联时代的必然产物,这座国际化都市每日吞吐数十万人口,连接着世界每一个角落,病毒沿着全球化的血管悄然而至,它不遵守护照签证的规定,也不理会国界线的划分,北京疫情的所谓“开始”,实则是全球疫情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显现,是高度互联世界的必然代价,这种空间上的无限延展性,使任何试图将疫情局限于某一地理起点的努力都显得苍白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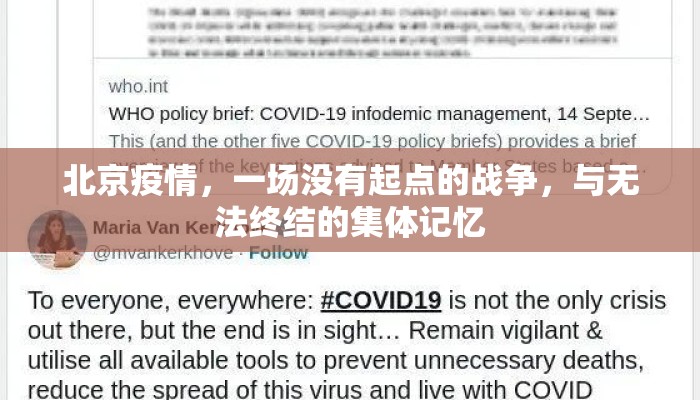
更为深远的是,北京疫情的“起点说”遮蔽了结构性脆弱,为什么是北京?为什么是那时?答案不在某个具体时间点,而在城市治理、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社会应对能力的复杂互动中,疫情像一面无情的放大镜,照出了城市生态系统中早已存在的裂隙——人口密度、居住条件、就医流程、信息传递机制,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疫情爆发的潜在条件,将焦点局限于“何时开始”,无异于回避了“为何会开始”这一更为尖锐的质询。
从集体记忆维度审视,对疫情“起点”的执着追问,折射出人类对创伤事件的心理应对机制,我们为灾难设定起点,潜意识中也在期盼它的终点,这种时间锚定成为集体疗愈的一部分,通过将混乱的经历纳入有序的时间框架,我们试图重获对生活的叙事权,北京市民对疫情“何时开始”的关注,背后是对“何时真正结束”的深切渴望,是对重回正常生活的无声祈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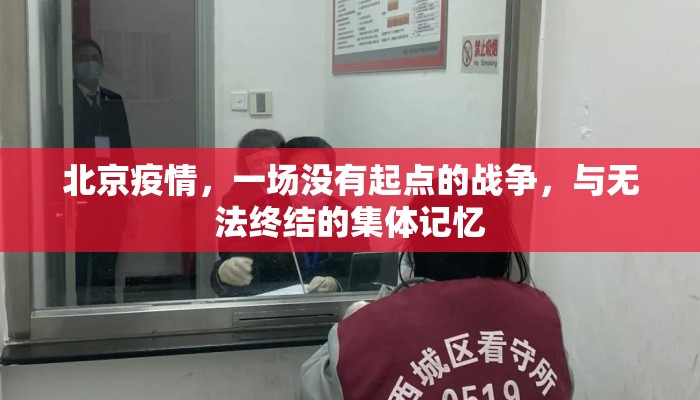
两年多来,北京疫情经历了多轮起伏,从新发地市场到冷链传播,从德尔塔到奥密克戎,每一次波峰都被标记为新的“开始”,形成循环的时间体验,这种疫情时间的循环性,打破了我们习惯的线性进步史观,揭示了现代文明与传染病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站在今天回望,对北京疫情“何时开始”的追问,价值不在获取一个简单日期,而在于促使我们反思如何理解灾难、时间和记忆,真正的智慧或许在于接纳疫情没有清晰起点的事实,认识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风险遍布的互联时代,北京疫情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开始”,它只是全球生态变化、人类生活方式转变的一个显现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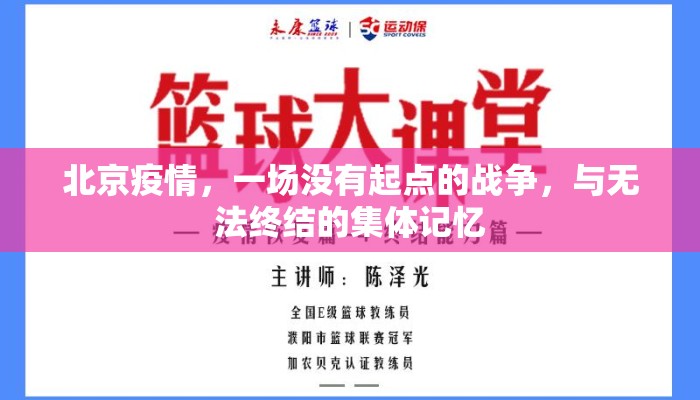
这座城市与疫情的斗争,早已超越了寻找起点的阶段,进入了如何与不确定性共存的深层探索,在无数个核酸检测亭的灯光下,在疫苗接种点的长队中,北京正在书写一部没有最终章的疫情史诗——这不是关于开始的记录,而是关于坚韧、适应与前行的叙事,或许有一天,当我们不再执着追问疫情何时开始,才是真正走向疫情终结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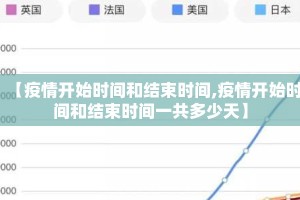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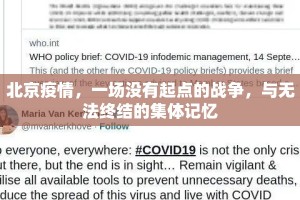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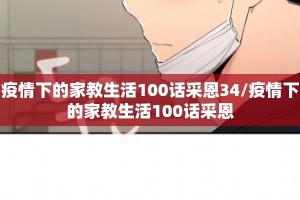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