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什么时候开始的封城的/疫情什么时候开始的封城
2020年1月23日10时,这个坐标本应沉入历史数据的深海,却像幽灵般盘踞在人类集体意识的表层,成为一个无法磨灭的创口标记,武汉——这座千万人口的巨城,以一种悲壮的决绝,按下了暂停键,街道被抽成真空,繁华沦为布景,只有救护车的嘶鸣划破凝固的寂静,世界在屏幕另一端,带着震惊与一丝侥幸的疏离,目睹着这现代史上从未有过的孤城绝境,他们不知道,这并非终点,而是一场全球性漫长仪式的残酷序幕。
执着于为全球疫情“封城”寻找一个绝对的原点,本身就是一种认知陷阱,是秩序对混沌的徒劳驯服,时间并非利刃,而是一片模糊的血肉,在武汉的官方决断之前,病毒早已撕开时空的经纬,2019年末,武汉医院里那些焦灼的咳嗽与异常的CT影像,是它无声的宣言;更早之前,它已在某个未知的宿主体内完成了致命的蜕变,将“开始”钉死在某一日历上,无异于用纪念碑的整洁,去掩盖一场爆炸最初的、弥漫的尘埃,我们所标记的,从来不是起源,而是人类认知系统被彻底击穿、被迫承认灾难存在的那个耻辱性瞬间,封城,是我们社会躯体对无形入侵者产生的第一阵剧烈免疫痉挛,是文明对失序的惊恐回应,而非灾难本身的开端。

这场以健康为名的全球大禁锢,迅速异化为一座巨大的隐喻性监狱,砖石被替换为绿码、行程卡与核酸报告,牢房是每个家庭单元,狱卒则由我们彼此扮演,监视被技术精致化,并被善意所包装,我们自愿上交隐私以换取虚幻的安全承诺,热情地参与这场数字圆形监狱的构建,最深的恐惧并非来自病毒的致死率,而是来自社会的排斥——那一道红码,或一纸阳性报告,便能将个体变为现代“麻风病人”,被放逐于系统之外,这种规训如此成功,以至于解封多年后,我们仍下意识地在公共场所保持距离,在与人交谈前摸向空空如也的口鼻,仿佛脸上仍烙印着无形的口罩,封控从未真正结束,它已从政策内化为我们的第二本能,一套刻在神经回路里的创伤后应激秩序。
当物理的城门重新开启,心灵的封锁却进入了加时赛,对“开始”的执念,折射出一种深层的修复式怀旧——我们渴望回到一个“纯净”的、病毒不存在的前封城时代,但那个伊甸园纯属幻象,灾难并非外来之物,它恰恰是我们所建造的全球化高密度文明体系的必然阴影,追问“疫情何时开始”,实则是在追问系统何时出现可见的故障,而拒绝承认系统本身早已埋下崩坏的种子,这种怀旧是精神上的止痛药,它让我们沉溺于对失去的“正常”的哀悼,却逃避了对这种“正常”本身(那催生了病毒并加速其传播的贪婪、扩张、失衡的现代性生活)进行任何严肃的清算,我们集体罹患了某种创伤后失忆症,精准地记住了封控的憋闷,却匆忙忘记了为何不得不如此。

封城的时间性,本质是一种权力的书写,谁有权定义“开始”,谁就掌控了灾难叙事的舵盘,这定义成为政治角力的场域,成为推诿责任的罗盘,成为塑造集体记忆的模具,不同的国家,根据其应对的成败与意识形态的需要,精心绘制着各自的时间线,将一场全人类的悲剧切割成彼此指责的碎片,这场记忆战争没有硝烟,却决定着未来我们将被怎样的故事所统治。
站在风暴眼之后的虚假平静里,追问“疫情封城何时开始”已是一个意义凋零的问题,真正迫切的诘问是:它何时才能在人类的灵魂中真正终结?当口罩不再是面孔的组成部分,当“隔离”变回一个陌生词汇,当我们将目光从对零号病人的无尽猎巫,转向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脆弱性的坚韧修补,转向对科技伦理的审慎重建,转向对人与人之间被撕裂的信任的缓慢编织。

这场封城从未局限于地理的围城,它是一场文明的试炼,城门洞开与否,从不取决于一纸公文,而取决于我们是否敢于直视那场集体高烧在文明肌体上烙下的所有疤痕,并最终领悟:最大的封锁,从来是对于反思的自我封锁;而最终的解放,必然是记忆与理性对恐惧的彻底超越——那一刻,才是人类时间重新开始流动的庄严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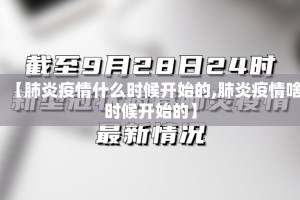



发表评论